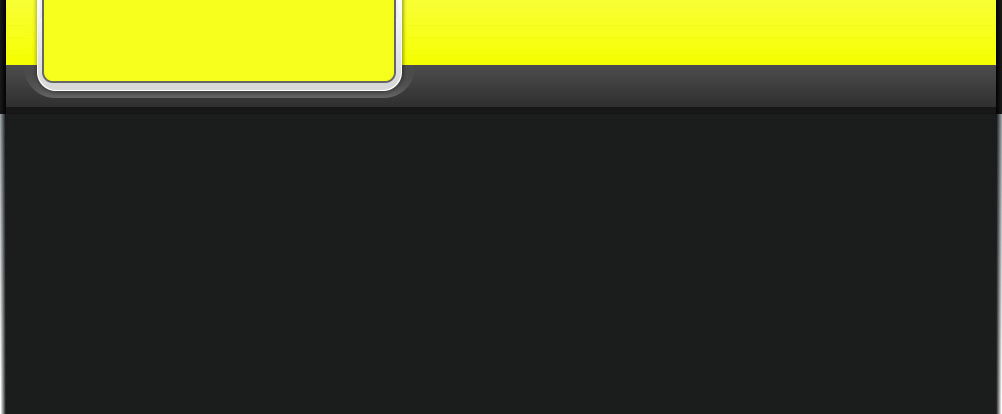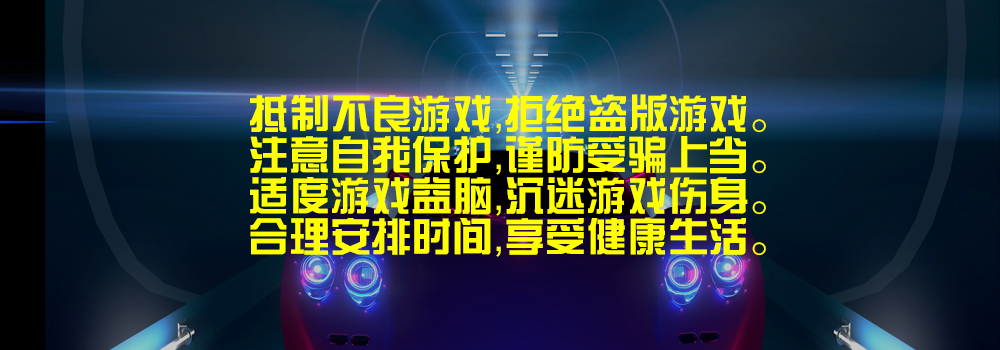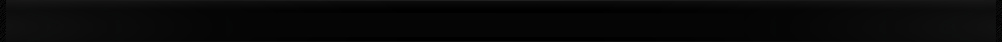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在1917年似乎突然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机:那个在东线消耗了它过多力量的沙俄帝国,因为内部的革命在这一年的年末轰然坍塌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猜测德国是否会在第二年春天冒险攻击西线。 因为在俄国获得的胜利,使他们有能力向西线补充新的部队和大量的战争物资,从而让德国在西线的力量大大增强。
至于鏖战了三年多的法国和英国,前者在经历了凡尔登的磨难和1917年4月尼维尔攻势的失败后,军队因为过于惨烈的伤亡而爆发了严重的叛乱,已经被大幅削弱以至于不再被德国视为主要威胁了。
英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1916-1917年索姆河和伊帕尔河造成的损失,同样耗尽了它的精力。但协约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仍旧非常明显:
德国的人力储备正在迅速减少,它的经济令人震惊,各种各样的原材料稀缺,人们也陷于厌战的情绪之中。更为致命的是,美国已经在1917年4月参战了,虽然它和英国一样,将自己的军事潜力转变成实打实的士兵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但这也意味着,到了1918年的夏季,数百万完成了招募、装备和训练的美国人会出现在西线战场上。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很清楚,如果德国不能在美国人真正参战之前结束战争,它就会被打败的。而此时抵达欧洲的美国军队正和协约国就军队是否独立作战问题互相扯皮——双方的分歧为德国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如果德国人能在美国的援助到来之前将英国和法国军队彻底击溃,这场战争就赢定了,因为远隔重洋的美国不可能单枪匹马跑到欧洲来继续和德国作战。(注1)
胜利的关键取决于德国军队能否在下一个回合给予英法联军致命一击。在1918年初成为德军统帅的鲁登道夫将军向国会展示了他的天才计划,并坚信这场在西线个月内为德国带来和平。
因为只有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下,接下来一切才会水到渠成,德国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和西方大国谈判,协商如何结束战争了。”
鲁登道夫的计划是一个明确而具有革命性的尝试,在对1917年的战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后,他和参谋们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战术体系,打算通过创新的突击战术来夺取决战的胜利。这种战术的首要因素就是就是突然性,然后要找出敌军防御阵地的薄弱点进行突破,要避免陷入对强大的防御设施的持续攻击。并要求迅速、猛烈而深入地扩大突破口,并自始至终地进行火力支援,以维持攻击的势头。
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班”这个陆军最小单位的创造性运用。在德军1918年春季攻势之前,班这一级别的编制只不过是陆军内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存在的唯一价值是为了便于基层行政管理和机动中纵横队的灵活变换。
但在鲁登道夫和他的参谋团队的改革下,德军的步兵班(大约14-15人,相当于半个排)得到了一支或者几支自动/半自动的武器和轻型迫击炮,并以此形成了其他步枪手进行机动时的火力基础。
当步兵班实现了火力和机动的结合后,这个单位就摇身变成了连排级编制内的一个独立战术单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术革命——从这一刻开始,步兵班就可以在自己的火力掩护或压制下进行机动作战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没有团级或师级的火力支援,大家都只能趴在战壕里站桩输出。
而这种战术被进一步扩大运用到了营、团和师级单位后,每一级都变成了具备特定战斗能力的战术单位。(注2)
为了让每一个进攻的步兵班变成独立的矛头,每个班都会得到一支自动步枪(或轻机枪)和一门轻型迫击炮,还会得到一支榴弹发射器(这种武器和法国人1916年装备的维维安-贝西尔发射器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分配给每个步兵的手榴弹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这种机枪交战双方都大量采购,图中是一个标准的英军机枪小组,射手+2名弹药手。
营一级的支援火力,除了原有的重机枪连外,还配备了轻型火炮,用来进行近距离的直接火力支援。至于被众多中文互联网小作文津津乐道的MP18冲锋枪,这种产量有限的自动武器还真不是德国总参谋部倚重的杀手锏——德军真正寄予厚望的,是全新的炮兵战术和与之相配合的新型步兵战术。(注3)
早在1917年的秋季,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就指挥部队在东线的里加成功突破了俄军坚固的阵地,而当时指挥炮兵作战的奥尔格·布鲁赫米勒上校,也正是在里加战役中首次运用了新的炮兵战术。
新的步兵战术则规定,在大炮停止射击之前,冲锋部队要尽可能地接近敌军阵地的第一道防线,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发现的任何间隙向前推进,并且用精心准备的信号系统标识出敌方防线最薄弱之处,然后由大批的步兵、骑兵和大炮在后面发动攻击。
但这种新战术和传统战术最大的区别在于接下来的阶段:打开缺口后,突击部队被命令不得停留在原地扩大缺口,而是要继续冲向第二道、第三道防线——这也是为何这种进攻战术被称为渗透战术的根本原因——为了保证火力和机动性,突击部队通常会携带较轻便的麦德森机枪或是帕拉贝鲁姆机枪。
跟在突击部队后面的常规步兵部队负责向左右两侧拉大缺口,攻占两侧的敌军阵地;迫击炮和重机枪交由他们来携带。所有参加攻击的部队都需要自行携带足够几天使用的弹药和补给,当他们的攻击力达到极限后,将会被新的部队“接替”。
只有那批经过了专门的步炮协同推进训练,负责进行最艰巨的防线渗透突击任务的部队,才有资格被称为“风暴突击队”。
而新的炮兵战术则是要求大炮要先在远离前线的射击场试射,等到进攻即将开始的时候才正式被部署到进攻炮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进攻还没开始的时候就长时间轰击敌军阵地——这不但是在告知敌人,军队将在哪个位置发起进攻。同时长时间的炮击也会让地面无法通行,从而导致后勤车辆和大炮都没法跟着步兵向前推进。
无论是新的步兵战术还是经过改良的炮兵战术,参加攻击的部队不经过训练显然是无法掌握的,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炮兵的射击和步兵的进攻要怎么配合到一起。
于是从1918年初开始,鲁登道夫就命令准备参加进攻的部队逐营离开前线,到专门的军队训练场接受相关训练。同时, 各团、各师的参谋部也接到命令,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尽可能靠近战斗地 点,也就是必须在最靠近战线的地方进行指挥。但相应地,鲁登道夫也给了这些参谋部更大的自主权,目的就是为了更高效地执行渗透战术,将旧有的逐级传递命令的指挥方式变为了更灵活和主动的任务式指挥。
也正因为德军采用了全新的炮兵战术,被选作主要打击目标的英军根本想象不到,德国佬的火炮密度排列得有多么丧心病狂:德国人在进攻区域内集中了6608门大炮和3534门重型堑壕迫击炮,平均每75公里就布置了大约100门大炮和50门迫击炮。
当1918年3月21日凌晨4点40分,德军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时,打击强度自然也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在战后各位亲历者的回忆中,如此密集的火焰风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够超越:
短短5个小时内,德军在西线万枚炮弹,这比整个普法战争期间消耗的炮弹总数还要多。而英军在1917年11月发动的佛兰德进攻战中,打完相同数量的炮弹用了足足两个星期!
德军进行的铺天盖地,无处躲藏的猛烈炮击最为毒辣的一点在于,他们还发射了相当数量的毒气弹。这种毒气弹的攻击方式被德军内部称为“彩色射击”,不同种类的毒气弹装在不同的箱子里并用 各种颜色的记号加以区分:比如标有白色十字的催泪毒剂,标有蓝十字的毒剂会让士兵咳嗽、呕吐甚至出现严重的呼吸障碍但并不致命;而标有绿色十字的双光气和黄十字的芥子气就是不折不扣要人命的家伙了。
德军先利用不致死的白十字和蓝十字气体迫使敌军摘下面具,因为当时敌军使用的呼吸过滤器无法过滤这两种气体,所以受到攻击的士兵会因为感觉窒息而摘下面具,这时致命的毒气就混杂在普通炮弹里从天而降,让敌军惊慌失措,那些没有被毒死的也会恐慌地逃跑了。
凑巧的是,天气状况对这次袭击特别有利。3月21日的早晨,法国北部春冬季有名的大雾出现了,把整个防线裹得严严实实。这种潮湿而沉重的空气可以让德国毒气弹产生的烟雾长时间地笼罩在地面上,不仅让后方的英国炮兵几乎无法看清目标,也让前线的守军死伤狼藉。
那些好不容易进入防线或永固工事的英国步兵,则是看着德军部队的身影稀稀拉拉在浓雾中显现,让摩拳擦掌,打算用机枪好好收割一番的英国人吃惊的是,数十万的德国进攻部队,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排列成长达数公里的横队,而是分散成了一个个10人左右的“突击小队”。
他们不必再死板地执行后方将军们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而是随时听从现场军官的指挥,利用沟壑或其他天然掩体做掩护,各小队快速奔袭,绕过并从背后攻击英军的机枪据点,打击后方以为自己不在任何步兵攻击范围内的炮兵阵地。
在大雾的掩护下,德军往往逼近到了手榴弹的可投掷距离内才被敌军发现,“德国兵来了!”的惊呼声整天都回荡在英军的堑壕上空,进攻的第一天,德军就成功地用损失39929人的代价(阵亡+负伤+被俘),占领了200多平方公里的阵地。还给英军造成了38512人的损失,这个对比相当惊人,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西线进攻方损失的人数往往是防守方的2~3倍。
而且德军伤人数中有2/3是负伤,其中的大部分人日后还可以重返战场。但英国佬的大部分损失却是用一种屈辱的方式退出了战争:近21000人当上了战俘。
打了这么些年的堑壕战,德国人终于找到了最富想象力的新战术,而且还特别有效。消息传回国内,德国沸腾了,柏林的市民在窗户外挂上了国旗,教堂也敲响了钟声。兴高采烈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登上私人列车时高喊:“我们赢得了战役!”他还给所有德国的学龄儿童放了天假。
到了4月初,德军已经前进了40英里(约66公里),侵占了1200平方英里(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法国土地,但此时的德军其实已经没有余力按照计划向海岸方向推进了。
而遭受主要打击的英军,则继续保持着令人震惊的高比例被俘人数——在德国进攻的头两个星期里,超过90000人变成了战俘,这些灰头土脸的英国战俘被德国的新闻影片摄影师兴奋地拍摄下来,影像片段则和战斗场景一起在国内的大银幕上放映,似乎预示着对巴黎势不可挡的猛攻。
德军的这次推进,还把另外一种传奇的恐怖新武器带入了战场——当巴黎市民被一连串每隔20分钟炸响一次的巨大爆炸声吓得够呛时——巴黎大炮来了。(注4)
德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豪赌,那些损失不小的风暴突击队员们行走在早已变成废墟的土地上,艰难地迈过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弹坑,这些勇敢无畏的士兵在继续前进,因为德国已经无牌可打,就看哪支军队会率先将自己消耗殆尽了。
随着攻击纵深的加大,当那些风暴突击队开始脱离己方炮兵的射程后,德军攻击的势头就不可避免地放缓了,毕竟得到了炮兵支援的防守方更具优势。早在进攻的进攻的准备阶段,德军就已经考虑到了进攻部队会逐渐脱离炮兵的掩护,为此参谋部做了两手准备:
后续的步兵部队携带了轻型野战炮和安装在雪橇上的迫击炮,这样至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最前面的突击部队。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突击队尽可能地缴获敌人的重型火炮,使其变为自己的助力。
但所有的尝试和努力全都被德国人自己的运输和后勤支援能力打败了,德国的将军们考虑到了战场上的方方面面,并做出了种种改进来适应新型的进攻战术,偏偏对旧式的补给和运输方式无能为力。
到了4月5日那天,德国军队终于停止了前进。此时进攻部队已经精疲力尽,弹尽粮绝,还早已远离己方的炮火支援范围。英军和法军空军方面的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士兵在攻击机上用炸弹和机关枪袭击德国的地面部队,德军士兵只好长时间躲在隐蔽的地方。
而德军之所以会在后勤和补给方面出现如此大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自己:鲁登道夫这次选择的作战区域,正是德军1917年时向兴登堡防线撤退经过的地域。长时间的拉锯战再加上德军撤退时进行的焦土战术,导致这片地区早已被洗劫一空,进攻的德国士兵甚至连一棵完整点的树木都找不到,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在弹坑累累、战壕纵横、铁丝网密密层层、道路缺少、泥泞不堪的地区负重前进。
相比之下,英法部队还可以继续利用后方完整的铁路线调兵遣将,他们的大部队可以乘坐火车及时赶到任何一 处受到威胁的战线上,或者利用铁路线实施快速转移。
就这样,德军取得胜利的短暂机会在迅速丧失,而德军的高速推进还造成了一个指挥官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
这些好几个月面临食物短,天天靠着萝卜和一点点马肉吊命,精疲力尽的德军士兵,在发现了协约国军队撤走时遗留下来的什么法国红酒、英国朗姆酒、牛肉罐头、面包、果酱和饼干等美味食品就走不动道了。
后来许多人将德国的春季进攻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德军部队取得初步胜利后,就专注于抢劫英军和法军仓库里丰富的存货,以致战斗趋于停滞。事实上只是这支快被饿疯了的军队就地解决补给而已,因为拉胯的运输和补给问题,前线部队这么做,还可以减轻后勤部队运送弹药的压力。
随着进攻部队离己方大炮的射程越来越远, 进攻的势头就越来越弱。能跟上队伍的炮兵小分队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而伤亡的暴风突击队成员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德军还是没能实现至关重要的突破。4月29日,鲁登道夫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鲁登道夫又发动了四次进攻,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不仅仅是因为德国的炮兵仍旧无法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援,后勤供应也同样跟不上推进的步兵。而德国步兵也在一次次地作战损失中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尽管德国人在1918年的进攻中,战略上是失败了,但他们在战术上的创新却给协约国的司令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有样学样的协约国很快就将德国的战术稍作修改,并结合自己空军和坦克部队方面的优势,在同年7月发动了猛攻,这次进攻,一直持续到了11月11日双方停战为止。
1918年8月协约国反攻中使用的法国雷诺M17/18型坦克,它开创性地使用了360°旋转的炮塔。
当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和美国都不约而同地以1918年的德国战术革新为基础,开始来改革自己的陆军编制了。。。
注1:1918年春天,美国派遣到欧洲的军队总数已经有40万人了,但是在他们完成培训和战术指导前,是没法发挥太多作用的。
贝当(法)和黑格(英)更倾向于将美军编入法军或英军的部队,而美军总司令约翰·潘兴坚持要求让美军作为独立部队在特定区域作战。英法两国都希望用美军直接填充他们亏空很大的部队,但潘兴希望将美国在战场上的投入转化为政治筹码, 而这一点只有在军队独立作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注2:谈到一战时期德国的“风暴突击队”,很多作者都喜欢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这种班级战术小队的武器装备,其实这反而是买椟还珠了。因为风暴突击队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可怕的战绩,依靠的是先进的战术,而武器是根据战术需要来配备的,而不是反过来。
简单来讲,不是因为装备了自动步枪或冲锋枪,德军的步兵班就可以自动使用渗透突击战术,而是为了要实施革命性的穿插突击战术,才给他们配备诸如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轻型迫击炮这样的武器。
注3:MP18型冲锋枪在堑壕突击战中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武器一战期间的总产量也没有超过40000支(按最大估算),这么点数量投入到数百万人交锋的西线,又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呢?别忘了,某个德国大兵用冲锋枪清扫战壕的前提,是他能够活着冲过交战双方之间的死亡开阔地。
注4:巴黎大炮共有7门,口径是230mm(9英寸),很多人误把它称作“大贝尔莎”,以此来向刚刚继承了克虏伯的产业的富豪,大贝尔莎夫人表示敬意。
但实际上,真正的“大贝尔莎”指的是一战初期,德军用来轰开列日、那慕尔和安特卫普等坚固要塞的18英寸口径(约457mm)的短程攻城榴弹炮。
那个时代的后勤能力不足以支持大纵深突破,德军自普奥、普丹和普法战争之后,快速调动兵员和物资基本就是铁路,德国和西欧的铁路系统也支持这种战术。鲁登道夫的攻势胜在快,败也在快,没有铁路系统的支持,汽车和公路还不足以担起重任的1918年,快速进攻反而会造成之后的被动。上一年俄国的勃鲁希洛夫攻势和朝鲜战争的洛东江战役就是例子。
对头,这种情况,德国人无法使用惯常的铁路运输优势。所以后世的大纵深理论在一战时还是空中楼阁,原因就是机动性不足。大纵深的前提是机械化,至少要摩托化。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德军进攻的区域被双方拉锯战打成了废墟,无形中也阻断了正常补给线。
所以真正吸取了一战教训的只有德国和苏联,二战时期德国搞出来的闪电战就是立足于这种战术的改进和全面提升
沙俄帝国可不是年末才轰然坍塌的。开年就被社会民主工党赶下了台。然后临时政府和德奥继续打了快一年,还能有来有回。直到那个矮个子秃顶中年人被德皇送回彼得堡[大笑][大笑][大笑],经过一系列耍赖皮的操作,然后才是你们知道的酥鹅。鹅螺丝帝国的终结,和布尔舍维克没有半毛钱关系
德国军队依靠改革班组级别的武器装备配置和战术,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是,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