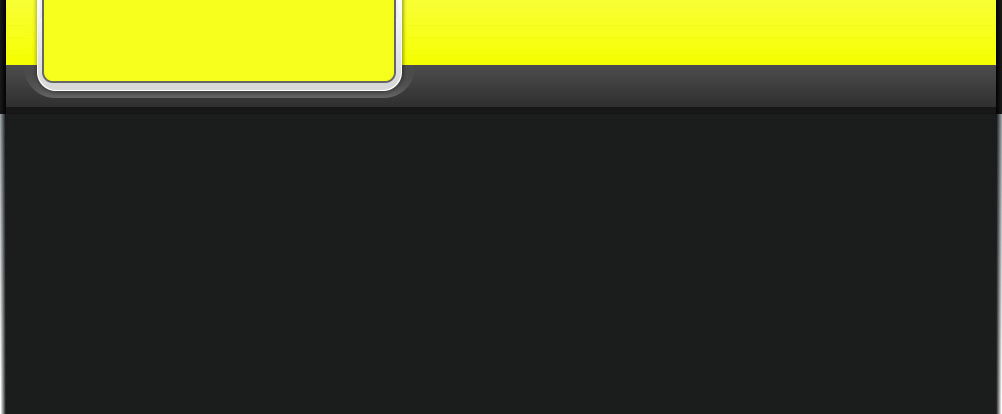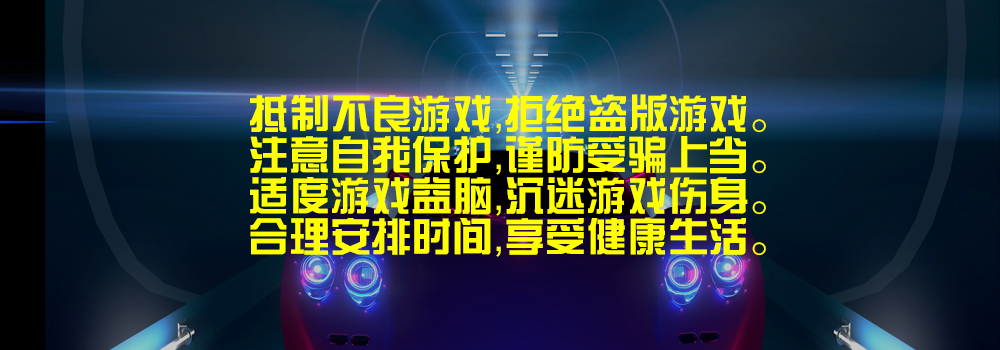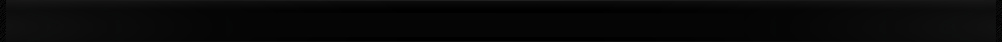在当今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们总是在探寻有效的投资策略以获取理想的收益。现实中,价值投资和华尔街正因为在风险和收益的定义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以至于在对待好生意被市场低估的时候,各自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认知视角和应对策略。
国联安基金价值投资组负责人杨岳斌认为,在价值投资的思维过程中,对于风险的认知并不来自于阅读年报中那些套路化的免责条款,而且往往是在经历的之后,才会对什么是真正的风险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
华尔街和价值投资中关于风险的定义有何不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五要素法(就是后期巴菲特不断提起的四个过滤器)该如何理解、实操中具体如何衡量风险,以下为杨岳斌通过对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实践经验的分析,系统性的论述了股票投资中的“风险”。
我们在上一篇《看破市场当中的“鸭兔幻象”—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视角对华尔街一些理念的分析》(以下简称鸭兔幻象)文章提到,考察一笔投资是否可行,当且只应当从风险、收益(Risk/Reward)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如果投资者对投资中最关键的风险和收益的定义最基本的理解都是模糊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那想要从风险收益性价比这个角度,来对投资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近乎于不可能。
现实中,价值投资和华尔街正因为在风险和收益的定义都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以至于在对待好生意被市场低估的时候,各自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认知视角和应对策略。许多价值投资者很早就关注到,巴菲特自上个世纪90年起,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华尔街的某些理论,似乎总是要与Beta或者Ebitda等这些华尔街术语过不去。不理解的人,一开始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在上一篇鸭兔幻象文章,针对Ebitda这个会计意义的收入指标做了一定的分析,解释Ebitda扭曲了费用支出,容易导致误判内在价值,从而遭到价值投资者唾弃。如何正确的分析和评判风险,这往往是投资过程中的最关键议题。
当一个好生意被市场严重低估的时候,价值投资理论的信奉者与部分信奉华尔街Beta,Ebitda理论的投资者(当然不是指全部),无论是在认知上,还是在具体应对策略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背后是因为,他们在风险的定义,衡量,以及理念层面,处处不一致。因此,我们密集搜索《巴菲特致股东信》上关于风险的言论,并且结合在价值投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一些经验体会,将风险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但又极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在本文做了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论述。
风险这个词,因为有着太多的应用场景,从而在定义上天然就有些含糊不清,诸如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交易对手风险、商业风险、政策风险、监管风险等等。据说,ISO国际标准组织甚至对风险做了40多种定义。这些风险的定义与金融投资中关于风险的定义显然是不太一致的。
股票投资风险是一种发生在金融市场中的价格风险。如果对于这个市场的风险认知不够准确到位,容易因概念不清而产生认知失调。如果在一个认知错误的基础上,还想进一步对一笔投资的风险收益性价比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几乎不可能。(为简便起见,本文后面所有提到的风险,如果没有特别强调,都是指股票投资过程中涉及的风险)。
在价值投资的思维过程中,对于风险的认知并不来自于阅读年报中那些套路化的免责条款,而且往往是在经历的之后,才会对什么是真正的风险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看和做,毕竟是两件事。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先生正因为经历了1929-1933年股市大萧条,遭遇几乎破产的浩劫。痛定思痛之后,他写出了价值投资奠基性巨作《证券分析》,定义了什么是内在价值(价值投资三大公理之一),而且是用Net-Net(计算在破产状态下的残余股东价值)这种极其保守的估值方法。之所以会采取这种谨慎的估值方法,就是强调本金安全的风险对于投资的重要性。
正因为看破了股市当中容易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他才说,买股票就是买生意(价值投资三大公理之二)这个看似平淡、实则振聋发聩之言。对于价值投资而言,投资者所承担投资风险无不与这门生意的内在风险紧密相关,而不是华尔街认为的股票历史波动性Beta。
价值投资认为是市场先生的情绪导致了每天的价格波动(价值投资三大公理之三)。这种认为股票价格深受人类心理活动影响的思想,较行为金融学提出类似的理论早了近半个世纪,和华尔街推崇的EMH(有效市场假设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几乎就是针锋相对。
在字典中关于风险的定义是: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格雷厄姆的定义是损失本金和相关收益的风险,巴菲特在继续注重本金安全的同时,还强调要考虑通货膨胀对实际购买力的影响。
在巴菲特1993年股东信中首次提出,通过五个要素的方法论来考察投资过程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经我们的研究和判断,五个要素法其实就是巴菲特后期一直在宣讲的四个过滤器的早期雏形。这是巴菲特投资框架的核心思想,四个过滤器是以一种清单式思维方式来分析投资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它分别是,好生意、护城河、德才兼备的管理层、内在价值(我们曾经在价值投资与ESG有机结合方法论系列做过阐述)。
我们很惊喜地在1993年股东信中首次发现了五个要素法。虽然二者存在着名称上细微的差别,但都是源自于格雷厄姆和费雪的思想精华部分,原则保持不变。 采取五个要素这种方法论来考察和甄别投资,的确是不可以对风险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但是,不应当因其约略模糊,就忽视这种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其不可替代性。虽然约略模糊,但却大致准确。
华尔街则给予风险一个全然不同的定义,认为一个股票或者一个组合的相对波动性是风险。这个相对性是指相对于股票全部整体的范畴。运用数据库和统计工具,华尔街计算出一个精确的贝塔,即过去股价的相对波动性,然后围绕着这个计算结果,建立起一套投资和资本配置理论。这种对于风险进行定量分析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准确,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如果是错误的,那对于指导投资又有什么意义呢?之所以,华尔街管基金经理叫选股票Stock Picker。而与之相对的,巴菲特说自己是选生意Business Picker?在我们看来,正是在投资中所采取了这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买符号化的股票,一个是买实实在在的生意,这就导致华尔街与价值投资在判断投资风险收益性价比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前所写文章中提示的鸭兔幻象,同一对象可被看成不同的事物。当人们把左半圆视为“鸭嘴”时,右半圆自动被纳入“鸭头”范畴;若左半圆切换为兔耳,则整体结构自动重组为“兔子“”轮廓。关键之处在于,从什么视角去观察这个现象,决定了最终会看到什么。华尔街看到了不停波动的股价。价值投资者看到的是好生意。
既然价值投资认为,买股票就是拥有一部分的生意。那么本质上,价值投资就是在分析一笔生意所隐含的各种风险,然后来分析这笔生意的投资性价比。投资一笔生意的风险可以来自负债方,譬如过度杠杆,以至于如果业务只是发生了轻微波动,都有可能因为高杠杆导致风险被过度放大,从而引发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价值投资并不推崇那些高负债企业的根本原因。
风险也可以是来自于资产方,来自于当投资者超出自己的能力圈,不能正确认知一笔生意的经济特征,从而导致无法看清资产的盈利能力,误判了全生命周期产出自由现金流分布的形态。最终,投资者因为高估了这个生意的内在价值,支付了太多的价格而亏损本金。不管是因为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导致投资者无法看清楚一个生意的经济特征,这样的认知错误并不能通过将模型里面的贴现率提升两三个点,就可以实质性降低风险。换一句话就是,投资者如果买了一个看似低估值的生意,并不能有效减少最后亏钱的风险。
在1993年伯克希尔的股东信里面,巴菲特明确提出价值投资五种要素法factors来评估风险。它们分别是:
考虑了一个管理层可以被评估的确定性,包括如何充分实现这个生意的潜在能力,以及如何正确的运用资金进行资本配置;
考虑了如何评估管理层是否将企业带来的回报正确地回馈给了股东,而不是给了自己。
1993年的巴菲特,就已经很清晰地指出,投资的风险与这个生意内在的经济特征紧密相关 。而且在我们看来,要素1中可以被评估这个词隐含了一个意思。那就是,这门生意客观上能不能被评估,主观上是不是在投资者的能力圈之内;要素2,3是要考察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是否德才兼备相关,需要看资本配置(3)和经营管理能力(2),较四个过滤器的表达更加具象化;要素5与这门生意所在国家的利率和税收环境相关。要素1、2、3和5对于风险的考量,最终都是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判断这门生意所产生全生命周期的自由现金流,以及它的内在价值。
这个时候,投资者才能比较有把握去判断一笔投资是一个划算的买卖,还是买贵了。这是要素4的核心意思。巴菲特的1993年提出衡量风险的五个要素法,在价值投资者看来,不过就是他后期反复强调的四个过滤器的一个变体而已,是价值投资在考察一笔生意时候的核心理论框架。
由此可见,价值投资的原则是保持基本不变的,是格雷厄姆和费雪的精华思想再现,不过表达方式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而已。也许只是这个时候,巴菲特还没有想到用四个过滤器来命名而已。
用五种要素factors(或者四个过滤器filters)的视角来看待风险。乍看起来,这种很大程度上是用定性的方式,对风险进行评估的方法,的确难以被准确量化。用这种方法来评估风险,对于华尔街来说会显得比较模糊。以至于,他们不可以像计算贝塔Beta那样,从历史数据库中得出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答案。但是,投资者不应当因为这种看起来约略模糊的分析方法,就忽视了它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
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看似不太确定,但在实践中却非常有用的思维方式,就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一小部分生意的内在风险,而完全不需要去参考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或者那些衡量历史的价格波动性表现的Beta或者西格玛。这就是“模糊的准确,胜过精确的错误”的本意。
巴菲特在1993年致股东信中感叹,难道真的有这么难去看清楚,拥有可口可乐这类好生意所承担的长期风险,远远好过拥有一个电脑行业或者零售行业这类生意所承担的长期风险。那种可以拥有全球品牌影响力的好生意,往往可以不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好生意品牌所建立的统治力,好生意产品所拥有的特殊秉性,好生意销售渠道的高效率,都会赋予这些好生意巨大的可持续商业竞争优势。在这些经济城堡之外,有一条保护经济城堡安全的护城河,给予了这些生意一种类似垄断地位的特许经营权。反之,很多拥有类大宗商品特征的生意,由于没有任何什么像样的护城河保护,不得不陷入日复一日的价格竞争,严重损害股东财富。
价值投资作为Business picker 和华尔街作为Stock Picker,在实操中至少存在8种不同理念上的冲突。也许还有更多其它的理念冲突,由于篇幅和水平所限,就不一一列举。相信大家在通读之后,完全可以总结出更多华尔街与价值投资在理念上所存在的冲突,从而对投资中的风险更好的判断。
华尔街定义一个股票或者一个组合的历史价格相对波动性是风险。根据过去股价的相对波动性,计算出一个精确的贝塔。在考察风险的时候,Beta理论并不在意一个公司到底在生产什么,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或者负债情况怎么样。甚至,对于华尔街选股者Stock Picker而言,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知道这个公司是什么名字(所谓的行业Beta投资,淡化Alpha的思想)。那些相信Beta贝塔的流派,并没有一种内在的机制能够让他们可以区分,生产单一呼啦圈这种大路货产品的玩具公司生意,与生产具有垄断地位的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生意,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风险的差别。但是,在价值投资者Business Picker看来,这两种生意的风险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些对消费者行为有足够理解的投资者,即使是一般水平的普通投资者,也可以很容易对上述不同的生意做出正确的区分,并且根据五种因素(四个过滤器)来判断这门生意长期竞争优势的强与弱。既然Beta无法区分那些普通生意之间存在的差别,那就更不要提那些好生意了。有时候,即使是那些见识很一般的投资者,也都能够轻易识别一笔好生意所能拥有的可持续商业竞争性优势。然而,这些好生意的贝塔,却和一大堆毫无竞争性优势的大路货的贝塔相类似。难道仅仅根据Beta的相似性,就可以贸贸然得出,那些极少数的好生意与一大堆大路货,具有完全一样商业竞争优势的结论吗?难道就可以推断,拥有这些大路货生意的风险,与这些生意所隐含的长期内在风险毫不相干了吗?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结论都是毫无意义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那种将贝塔等同于风险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Beta作为一个波动性指标会让华尔街投资者回避一个好生意。价值投资者反而喜欢波动性。正因为价格有波动,才有可能让价值投资者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真正好的生意。现实中,如果价值投资者面对一个同样是基于生意视角的谈判对手。对方往往会因为很懂得这笔生意的经济特征,非常在意自己的得失。价值投资者也就几乎不可能用一个特别低的价格去买下这个好生意很大部分乃至100%的股权。反而是在资本市场上,那些只在意Beta的股票投资者,也许会轻易将一个好生意以一个难以想象的低价格来出让。正如1973年,伯克希尔用1000万美元,大概以相当于25%内在价值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进了华盛顿邮报10%的股权。当时市场估计该公司的内在价值约在应该在4亿到5亿美元之间。2000年,伯克希尔持有华盛顿邮报市值达到10.64亿美元,这笔投资的阶段性回报几乎是100倍。
Beta理论所在意的只是这个股票过去的价格波动历史情况。而那些把股票当作生意来看待的人呢,显然是秉持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在价值投资而言,波动性最小的生意也许风险最大。一个回报率在20-80%之间波动的生意(譬如:一个内在价值在100-140之间的生意,买入价格是80),肯定远远好过一个雷打不动5%回报率的生意(譬如那种货币类的固定收益类投资)。虽然前一个生意的波动性也许远远大过第二个,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第一个生意风险更大。Beta绝不是衡量风险的工具。在高利率环境下,Beta很低的现金类产品,反而是风险最大的。价值投资注重本金安全,强调绝对收益,但绝不是完全投资到那些无风险的货币类资产。恰恰相反,价值投资认为这类资产从长期来看,风险最大,因为货币购买力会被通胀严重侵蚀。
价值投资认为,华尔街关于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的定义,相当具有误导性。价值投资从不会认为,一个投资的风险越大,所带来的收益越大。但是华尔街所流行的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中关于预期收益率和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来描述的。价值投资不会认为贴现率(收益)更高,会导致一笔投资的风险越大。如果正确判断了一个生意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分布,采取一个更高的贴现率,会得到一个更加保守的内在价值。这种使用更加保守的假设估算出来的内在价值,在逻辑上只会更加安全。价值投资从本质上来讲是风险厌恶,Risk Averse,喜欢的是风险收益不对称时候的机会。
价值投资者宁愿在99%时候,被人称之为保守,也不愿去冒那种1%的小概率事件,引发可能导致血本无归的风险。糟糕的是,华尔街关于风险度量所产生精确的错误,往往更加致命。因为精确的错误会带来盲目的自信,从而对投资的风险作出错误的判断。LTCM,美国长期资本公司,一群极其聪明的数学家,以及一群经验极其丰富的投资家,里面甚至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管理着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建立起VAR模型,声称从历史上的数据来看,只有百年一遇的风险才会导致他们的模型失灵。正因为这个风险判断,LTCM才建立起满满的信心去建立他们的套利模型。更加致命的是,LTCM采取的所谓套利策略由于并不是真正的无风险RISK FREE,需要配合巨大杠杆,把本来很细微的利率风险放大得无比凶险。金融市场不时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导致正态分布模型中的小概率事件成为了肥尾现象,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本金全部损失。具体关于LTCM的报道很多,这里就不再展开。只是举例说明误判风险的严重后果。
价值投资认为,风险与持有的时间相关。长期持有一个低估好生意对价值投资者来说很安全。但如果持有的时间太短,反而是风险巨大。市场短期是一个投票机,即使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也无法把握市场每天的变幻莫测。今天就算是买入一个十年看最好且被严重低估的生意,明天、下周、下个月或者下一年就卖出,这样的短线操作在价值投资看来反而很容易会亏钱。价值投资者推崇长时间持有一个好生意,是时间的朋友,是称重机。这与华尔街注重短线交易的做法就完全不一致。很多时候,华尔街投行所提供报告中的观点都是被污染过,带有明确导向性,目的只是为了更好促进短期交易所产生的佣金。巴菲特曾经在股东信中公开嘲笑华尔街Stock Picker经典语录,“投资者从不会因为止盈而破产(You cannot go broke taking a profit )”。因为,他们即使曾经拥有过一个好股票,在股价上仅仅只是涨了一小段以后,就会止盈出局了。在Stock Picker眼里,投资就是炒作,个股之间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Stock Picker不断加大股票的换手率,根本无法长期持有一个好生意。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波浪潮(或者叫板块行情或者Beta行情)。华尔街创造的轮动理论,让他们相信任何个股都会有被轮到的一天。
风险与一个组合的集中或者分散程度不一定有关。在价值投资看来,集中投资反而更安全,分散才是风险。基于Beta及Modern Portfolio Theory现代组合管理理论,华尔街认为一个组合要足够分散,而不是集中。他们提倡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价值投资则恰恰相反,认为鸡蛋就应该放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篮子里。如果投资者真的懂这门生意,能够看清这门生意长期的的经济特征,可以找到5至10个拥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的理论就显得毫无意义。风险往往与投资中涉及的变量多少有关系。一个越分散的组合,因为需要涉及更多变量,逻辑上有可能反而增加风险。价值投资者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投资者不去把资金放在他能够理解得最好的第1个生意上面,而是放在第20个生意上面。一个投资者最理解的生意,也就意味着最少的风险,同时拥有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集中投资这种策略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加注意去提升对于这笔生意的理解程度,并且可以在他买入之前,对他所买到生意的经济特征,可以提升到一个令他很安心和很确定的程度(注意,这个时候的能力圈的概念就会显得至关重要)。在价值投资看来,一个好生意可以有效对抗竞争。集中在好生意上长期投资,反而可以有效对抗过度分散的风险。
一个投资组合越是分散投资,往往意味着需要投资者关注更多的变量,对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圈往往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风险也将大幅度上升。对于华尔街来说,不断追求变化。对于价值投资来说,变化往往不是代表了机遇,而是意味着风险。而且,太多的变化很可能导致一个行业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被一些不可知的力量摧毁。这些变化要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竞争,要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替代,有时候甚至是彻底的摧毁。这将会导致投资者更难判断未来的经济特征。巴菲特认为如果线个big Idea核心观点上反而更安全,而不是更加危险。风险往往是那些来自于投资者不自知的风险,尤其是那些投资者实际上并不知道,但却声称自己知道的风险因素。如果不知道这个生意的经济特征,不清楚这个生意的FCFF的分布,即使把贴现率从7%提升到9%,也就是买得便宜一点,这种做法也不会带来任何安全边际。
1972年,美国国际象棋大师费希尔和苏联国际象棋大师斯帕斯基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比赛。当时人们设想,如果让最强的人脑和最强的电脑之间进行一场国际象棋较量,谁会是赢家?当时的计算机一秒钟可以进行数十万次的计算(今天的计算能力更强)。巴菲特先生关注到这方面的报道,并且评论说:研究证明人的大脑在未及思考的情况下,与计算机相比排除了99.99%的可能性。就运算速度和覆盖面而言,人类的大脑根本无法与计算机相比。但是,人脑可以拥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分组或者排除的能力。这本质上是,人脑在面对无数的可能性中,可以迅速排除大部分选项,进而找到几个真正大的成功机会的可能性。
价值投资通过采用四个过滤器的思维方式,迅速排除掉绝大部分的投资机会,让大脑专注于对极少数好生意的分析。反观华尔街的一些理论,则容易让投资者看不清楚一门生意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很容易使人过于密切关注一些短期热点事件,关注无效有时甚至是误导性的海量信息,从而导致大脑宕机。价值投资者则不然,可以专注于看清少数好生意中那些真正重要的和可被认知的(important and knowable)的变量,掌控其中的风险。诚然,每一个投资者都会犯错。但是,当投资者把自己聚焦在相对比较少的、且容易被理解的投资个案之中,背后是3-5个真正好的Idea。那么,一个完全知晓相关信息,并且勤奋的投资者,是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一笔生意的投资风险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价值投资只希望在少数几个好的Idea主意上显得聪明,而并不寄希望于在很多个需要好主意的生意上显得很聪明。Less is more,少就是多。
总体而言,价值投资认为,如果一笔生意的风险不能被很好的判断和分析,那么就不能正确判断投资的风险收益性价比,看不清一笔生意的内在价值。正因为在对待风险态度的定义、实操以及理念上存在着各种不一致,导致华尔街的Stock Picker和价值投资的Business Picker在对待好生意被市场低估的时候,各自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认知视角和应对策略。风险虽然不能被精确度量,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准确判断。价值投资者Business Picker拥有一个系统,不管称之为五个要素法还是四个过滤器,力争抓住少数的好生意。最终,更有可能长期战胜市场。
后注:为了更好地讨论和应对风险,我们翻阅了大量巴菲特致股东信,发现风险判断往往与概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除了需要具备正确的风险和收益的认知,还应当具备一定的概率思维去应对随时发生变化的环境。而且,投资最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候下注足够多,错误的时候敞口足够小。风险判断,往往与概率密不可分。为什么价值投资希望在进行一笔投资的时候有概率上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厌恶赌场)?如果风险不应当被Beta这个历史价格波动性指标来表达,那为什么也不应当用高斯函数的正态分布来表达,或者一个或者几个西格玛来表达?届时该文将简单陈述几个与风险判断密切相关的概率问题,以期写成鸭兔幻象-概率篇的文章以飨读者。